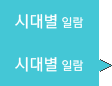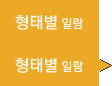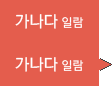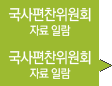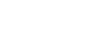今三月初五日大臣·備局堂上引見入侍時, 禮曹判書金鎭龜所啓, 頃日東萊府使狀啓, 對馬島所送禮單, 朝廷有依例回賜之物矣, 其後泰恒, 報于本司, 以爲島主所送, 非舊銀, 乃是新銀, 我國回賜之物, 亦當計劣減給之故, 臣以此有所陳達, 令廟堂覆啓, 其中人蔘·白木綿等物, 斟酌減送矣, 倭人, 見減數禮單而發怒, 故泰恒, 因倭人之發怒, 不爲更稟朝廷, 又傳, 前送禮單, 未免大段失誤, 而臣曹請推之外, 無他論罰之道, 大臣今方入侍, 下詢而處之何如, 右議政申曰, 朴泰恒處事, 殊甚無據矣, 禮物贈遺, 關係重大, 而不復啓稟, 任意徑給, 其不遵朝令之罪, 不可不論也, 且頃日渡海渰死人屍親等, 闌入倭館, 多般作挐, 自本府嚴責云者, 尤極駭然, 倭館之任意出入, 旣有禁令, 渰死人屍親, 雖曰, 情理痛迫之致, 何可任意闌入, 至於打傷倭人乎, 不可以屍親之故, 有所容恕, 而狀啓中, 只曰, 嚴責而已者, 此豈邊臣事體乎, 政院, 雖已請推, 決不可只施問備之罰, 拿問定罪似宜矣, 刑曹判書閔鎭厚曰, 屍親等私情, 雖云痛迫, 至於冒入倭館, 條制甚嚴, 而有此作挐之擧, 事極駭然, 爲邊臣者, 所當別樣痛治, 而只以嚴責之意, 馳啓, 只此一款, 亦難免罪矣, 鎭龜曰, 頃於倭人燔造之請, 不能據理退斥, 而至於累度啓聞, 亦不過驚動於倭人恐喝之言也, 旣不能奉行朝令, 而又不能禁防闌入, 邊上受任之臣, 豈容如是乎, 行兵曹判書李濡曰, 朴泰恒, 自初以渡海船敗沒事, 疑責太過, 至於屍親輩恣意闌入, 而旣不能禁防, 又但嚴責而已者, 殊涉疏闊矣, 且有他不稟朝廷, 處事顚倒之罪, 而此則不必備論曲折, 只以闌入一款爲主而拿問, 似可矣, 大司諫李健命曰, 渰死人親族, 私情雖矜惻, 任意作挐於館中, 極爲驚駭, 作挐之罪, 雖未知其律之如何, 而嚴責分付云者, 誠極緩疎也, 我國之人, 闌入館中, 而不爲嚴懲, 則藉令倭人, 闌出作挐, 亦何以禁止乎, 今若置之, 則復(後)弊難防, 且常時若爲禁飭, 則必無, 如許之事, 似當有論罪之道矣, 行副提學金鎭圭曰, 邊臣不遵朝令, 則他日之慮, 有不可言, 雖以禮單事言之, 禮官旣已稟啓, 廟堂又爲覆奏, 定奪分付之後則邊臣, 何敢不復稟告朝廷, 而徑先擅斷乎, 況我國人, 與彼國人, 私相往來, 禁條旣嚴, 則今此屍親等, 私情雖痛迫, 何可一任其冒入作挐而莫之禁戢乎, 如此邊臣, 若不重究, 則後弊可慮矣, 上曰, 不稟朝廷, 徑給別幅, 而至於屍親作挐, 亦不嚴戢, 俱極駭異, 稟問定罪可也, 閔鎭厚曰, 闌入館中, 打傷倭人之類, 亦令本道, 嚴査科罪何如, 上曰, 令本道, 査出啓聞, 可也, 右議政申所啓, 此則頃日東萊府使朴泰恒狀啓也, 渡海船營造監色, 則已爲覆啓, 使之推問, 而護行差倭論罪事, 未及仰達矣, 我國造船監色, 旣自我國査治, 則護行差倭, 亦不無不能看護之罪, 使館守倭, 通報島中, 論罪事, 亦爲分付何如, 上曰, 依爲之, 右副承旨崔重泰所啓, 擧行條件, 辭語之冗長, 未有甚於近來, 就其稟裁條件, 雖係尋常微細之事, 行語間支辭蔓語, 盡錄無遺之故, 文字浮張胡亂, 殊非古昔記語撮要從約之意, 中間亦以此申飭, 必令抄略啓下者, 非止一再, 而文具漸勝, 至于今日而極矣, 今後則筵席稟奏事件, 刪去其不緊繁辭, 只錄其切實緊語而啓下何如, 上曰, 古者注書, 詳其日記, 簡其擧行條件矣, 今則, 日記不詳而擧行條件甚繁, 承旨之言是矣, 申飭可也, 刑曹判書閔鎭厚曰, 古規則擧行條件, 雖撮其大略, 而日記冊中, 無不備載矣, 近來則一從擧行條, 盡書於日記冊, 而注書以出擧行條, 今雖從略書出於擧行條, 而日記冊則必須詳載之意, 似當別爲申飭矣, 重泰曰, 日記則申飭注書, 詳悉載錄, 而擧行條件則抄略其梗槪, 要使其條落分明易見則足矣, 上曰, 日記冊則詳錄, 而擧行條件則略之可也, 行副司直李寅燁所啓, 前以江都移轉未收之散在畿邑者, 移納山城之意, 仰達矣, 其未收之在水原者, 當爲五百四十餘石零, 而水原, 爲畿輔重地, 軍兵亦幾至八千名, 不可不別爲顧見, 而聞全羅監司閔鎭遠之言, 則卽今本府無一日之軍餉云, 誠爲寒心, 本府移轉之當納山城者, 待秋收捧, 於本府, 留作軍餉, 似爲得宜, 故敢達矣, 上曰, 依爲之。